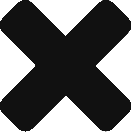在賓州的隔離已經三週多了。上星期出門買菜,沿途經過一棵盛開的櫻花樹。櫻花三百六十度地向外開展,下垂的枝枒向著地面形成一個粉紅的穹頂—好久沒有看見充滿生命力的樹與花!
我嚮往那粉紅,說不太上來為什麼自己一心被吸引著,明明以前總是嫌棄粉紅色,覺得那不是意味著豔麗俗氣,就是過度嬌柔可愛。但是這棵櫻樹的粉紅不一樣,那是一種趨近於白玉色的粉紅,那種顏色訴說著一種平凡與輕柔,是這個充滿死亡與恐怖的世界需要的一點可愛。
櫻樹一直映在我的腦海裡,太想念它了,隔天於是漫步三十分鐘去找這棵樹。其實比起「想念」,那時候的心情更像是一種「不捨」,因為知道櫻花一年就只有短短幾週的開花期,盛開之後花瓣就會漸漸凋零,櫻樹馬上就會長出綠葉與枝枒,開始新一季的生命。其實櫻樹的生命還在繼續,是自己自私地想要把握那片刻粉紅,不捨是一種自作多情,把一部份的自己投射進那無窮無盡、自然而然的天地。
看見盛開的櫻樹,想起了國中時讀到席慕蓉「一棵開花的樹」。這首詩大概是席慕蓉最廣為流傳的作品,大抵講述的是單戀的心情,那盼望愛有所回歸、相依疼惜的情愫。那棵開花的樹或許不是櫻花樹,但詩中描述花瓣凋零一地的樣子,那倏忽、不能把握的美好,讓我不小心將自己青少年時對詩的印象還有那不成熟的憂鬱投映在賓州鄉間的的櫻樹上。
雖然是一種自作多情,但這種移情讓隔著時空與海洋大陸的分隔的年少自己,能夠與此時此地的自己連接。我珍惜這樣的片刻,它們讓我明白,成長個過程雖然不是線性連續的,卻偶有相呼應的時刻,像是在自己單薄的體內裡製造回音,不同頻率的敲擊與發聲,我也變成了能夠裝下不同時空的自己的容器。
再過幾天,應該就看不到這那株盛開的櫻花樹了。我好奇想著,花真的離開這個世界了嗎?真的就永久消逝了嗎?或者花其實無所謂。當我們像是在黑暗中等待疫情的結束,櫻花無所謂等待,就只是往復循環不息的天地裡的一瞬。含苞、綻放、飄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