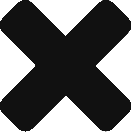文|張依婷
女人迷 Womany 2019/05/28
唯有在理解到我們任何人都有可能錯讀文學,成為思想畸形的加害者、性暴力的被害者、倖存者,我們才以可能能更用心活著。並且如同奕含曾說的:對他人的苦痛有更多的想像力。
今年我二十六歲了,是作家林奕含結束生命時的年紀。兩年多前奕含離世的新聞震驚社會,與事件相關補教名師受到多方譴責,也抖出了台式升學主義、補習班文化與父權體制交織生成,使得台灣的中學生(尤其是女學生)處在極脆弱的位置。奕含的驟逝也讓許多女性讀者經歷了集體創痛,還記得我當時讀到了許多朋友或陌生人寫的悼文,字句中充滿了對作家的思念還有對父權暴力的憤恨與斥責,更多的是無能為力的傷感。
作家的聲音不復在,留下遺作《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雖然小說許多部分是奕含本人經驗的擴寫與再編織,但藉由文學創作,奕含似乎讓她自己以及讀者透過文學的距離去評判整個事件,感受加害者、受害者與倖存者的心理。兩年過去了,沒有人能從這件事情中全身而退,也沒有人能被救贖,但我們能夠透過重訪這本小說,思考這本書對於當今的台灣社會的意義,以及文學(包括閱讀與創作)在這整件事情中所扮演的角色。
奕含在一次訪談中提到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不是一本只談論女孩子被誘姦、強暴的控訴之書,而是「關於女孩子愛上了誘姦犯的故事。」這樣的詮釋讓我們重新思考房思琪這個角色在故事中擁有的自主權與愛人的能力,而這樣的能力又怎麼被父權社會壓抑、利用了。探討思琪的自主權並不是幫小說中的補教名師李國華脫罪,而是思考在父權社會之下,我們沒有一套語言去訴說少女對於愛戀、身體以及性慾的自主想像。台灣的傳統倫理告訴我們女人以及少女的慾望是要被約束的,我們的身體必須被遮掩,我們的慾望與愛人的能力像是令人羞恥的標記。李國華大概也是利用了思琪對自己情慾的羞辱感,而能將性暴力合理化為情愛,他想:「他喜歡她的羞惡之心,喜歡她身上沖刷不掉的倫理,如果這故事拍成電影,有個旁白,旁白會明白地講出,她的羞恥心,正是他不知羞恥的快樂的淵藪。射進她幽深的教養裡。用力揉她的羞恥心,揉成害羞的形狀。」。無論是情愛還是暴力(或是兩者的混合),在一個強調女性節操、個人尊嚴的社會裡,都被化作不能向旁人訴說的秘密。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裡的李國華、班主任蔡良、受害學生郭曉奇等角色都映射了台灣補教生態的實況,但這部文學作品不只是透過寫實情節傳遞殘酷的訊息,令讀者同時感到耽美與駭慄的是作者的文字本身。雖然小說被幾位前輩作家評為時而工筆過細、句式略顯「老派」,像是使用了六、七零年代的創作手法,但如同奕含在訪談中提到的,《房》其實是一部用詞新穎、在許多處刻意誤用典故以製造張力的文學作品:「比如說,我說溫良恭儉讓,溫暖的是體液,良莠的是體力,恭喜的是出血,而讓步的是人生,然後你看到這裡,你應該知道溫良恭儉讓的溫,它絕對不是指溫暖,它是指『君子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溫』。⋯⋯所以文字的張力在那裡,張力在它明明不是溫暖,可是我硬是把它寫成了溫暖。」乍看之下是五式排比句,但實際上是透過思琪的眼睛去檢視李國華歪斜的思想體系。這不只是少女對性侵者憤怒的控訴,更散發一種對於文學作為複雜的語境建立、被挪用而能夠成全惡意的挫敗感。
奕含的文字世界像是個映照著夜色的琉璃:精緻綺麗,脆弱詭譎,好像稍不小心,瑰麗精準的文字底下的惡意—李國華的惡意、父權社會的惡意、性與精神強暴的惡意——就會傾洩而出。美與惡的疆界被混淆了,而這也是奕含透過她的文字藝術想要傳達的訊息,如同她在訪談中提到的,雖然這部文學作品中充滿了想像的情節,但是讀者感受到的美感以及痛苦都是真實的,而這不容質疑的真實感受都是透過文字與修辭構築而來的。小說仔細解剖審美的快感,反思這種對於藝術與美的渴望,成就了故事中李國華的學識的淵博,也讓他能一邊玷污世界、強行佔有,卻又能夠以真善美來自圓其說。文學與藝術,是不是最後只是一種表演?還是許多人用來精神自慰的花言巧語?我們鍾愛的文學與美,是否在某些時刻只是成全了父權世界中所追求的精神境界—那些男性想像中的磅礴意境、征服與掠奪?
讀完《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以後,我一直在想作家寫道「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是房思琪式的強暴」是什麼意思。我想除了毫無解脫之道、不斷重複的性暴力本身,大概還有一種整個靈魂徹底被掏空的感覺,讓一個人無法成為「人」,無法成為自己。於是生命還沒終結,卻早已萎靡腐爛,像是思琪最後飽受創傷折磨、不能自理的狀態。但與這種高強度的撕裂同樣駭人的,是促使暴力、合理化暴力的漂亮說詞。惡意與粗暴於是被包裝成甜甜的糖果,是保護、是關愛,包裝紙上寫道妳被汙了、被插爛了都是妳的錯,世界不會幫妳、傾聽妳,卻只要妳訴說滿滿的歉意。房思琪式的強暴不只是性暴力而已;在身體與精神被剝奪的同時,這樣的暴力除去受暴者控訴與表達自己的能力。無能訴說、不能駕馭語言與敘事,事件就好像不存在一樣。而這樣的暴力,在許多地方都正在上演著。
奕含了解這種暴力的規模與質量之大,以及它的不可消滅性,也因此在訪談裡談及:「我在寫這個小說的時候會有一點看不起自己,那些從集中營出來,倖存的人,他們在書寫的時候,常常有願望,希望人類歷史不要再發生這樣的事情,可是在書寫的時候,我很確定,不要說世界,台灣,這樣的事情仍然會繼續發生,現在、此刻,也正在發生。我寫的時候會有一點恨自己,有一種屈辱感,我覺得我的書寫是屈辱的書寫。」屈辱的原因,在於作者了解到文學本身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這個世界的暴力並不會因為房思琪的故事廣為流傳而消失。在這種規模與質量巨大的暴力面前,文字與文學似乎顯得軟弱虛無了。
雖然是屈辱的書寫、雖然評判了文學藝術的有限,奕含的創作也同時駁斥了文學作為巧言令色之展演這個論點。文學作為有心之人的工具雖是《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極力探討的事件,但我想這並不全然是小說的結論。小說探究文學與知識造就的思想畸形,恐怖深淵之中也叩問「倖存」的意義以及「閱讀」如何作為我們傳遞、修補、重訪創傷的工具,就像故事裡的怡婷、伊紋透過閱讀窺探思琪的回憶,或是我們這群讀者通過這個故事認識奕含,理解性暴力與精神病污名化的摧毀力。
我們不會有人因為讀了這個故事獲得救贖,或許妳也能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在某種程度上揭露了、製造了更多創傷。然而,我們可以試問,奕含在身心煎熬的狀態下完成的「文學」與李國華或是其他有心之人高談闊論的「文學」,兩者之間的差異是什麼。精細的工筆與耽美的語境,於前者是對文學的抒發與摧毀之力的沉痛省思,是對藝術、慾望、暴力的反覆刻畫;於後者是自戀高潮的啟動工具,是膚淺浮誇的裝飾品。唯有在理解到我們任何人都有可能錯讀文學,成為思想畸形的加害者、性暴力的被害者、倖存者,我們才以可能能更用心、小心地活著,感受每一個善念與惡意迸發的一瞬之間,並且如同奕含曾說的:對他人的苦痛有更多的想像力。二十六歲的我,帶著房思琪的故事,也才敢說自己真切活過。